(一)故乡的那串“珍珠”
文学总爱把一汪或一池水比作珍珠,亮晶晶的,真像。从天上看,更像,例如航拍什么的。
家乡也有几汪水,不过叫法没那么雅致,没那么好听,叫“坑”。坑:凹下去的意思。活埋也叫坑,焚书坑儒;陷害也叫坑,坑诓拐骗……似乎“坑”,并非褒意,也无美感。
那些年,村村都有几个坑的,那是用土,或起石挖掘而成,因年年都有人用土,隔年还要挖回坑泥,那是庄稼的上好肥料,坑就逐年扩大,逐年加深,有的几米十几米,一个猛子扎不到底。

坑,虽无珍珠之类的叫法那么雅致,那么文采,但在过去的那段年月里,却是村人们须臾不可离开的伙伴。夏天,坑里洗澡;冬日,坑面上滑冰;平时,坑崖四周,总有一圈妇女们在洗衣裳;晚间,坑边的大柳荫下,拉领破席,摇面蒲扇,又是大家乘凉,谈古的最好场所……哪个村子有汪大坑,用现在的话说,就是村里的文化娱乐中心,如建设美丽乡村的文化体育广场一般。
不过我们辛绪村的大坑,与其他村庄的大坑尚略有不同。别村的大坑,大多零散的,星罗棋布的,我村的大坑则是被一条季节性河流串成串的,那条只有雨季才有水的河流,从东山里汇集雨水而来,经陶庄村,入蛄蝼沟,然后流入我村的几个大坑,胡家坑、张家坑、乔家坑、仇家坑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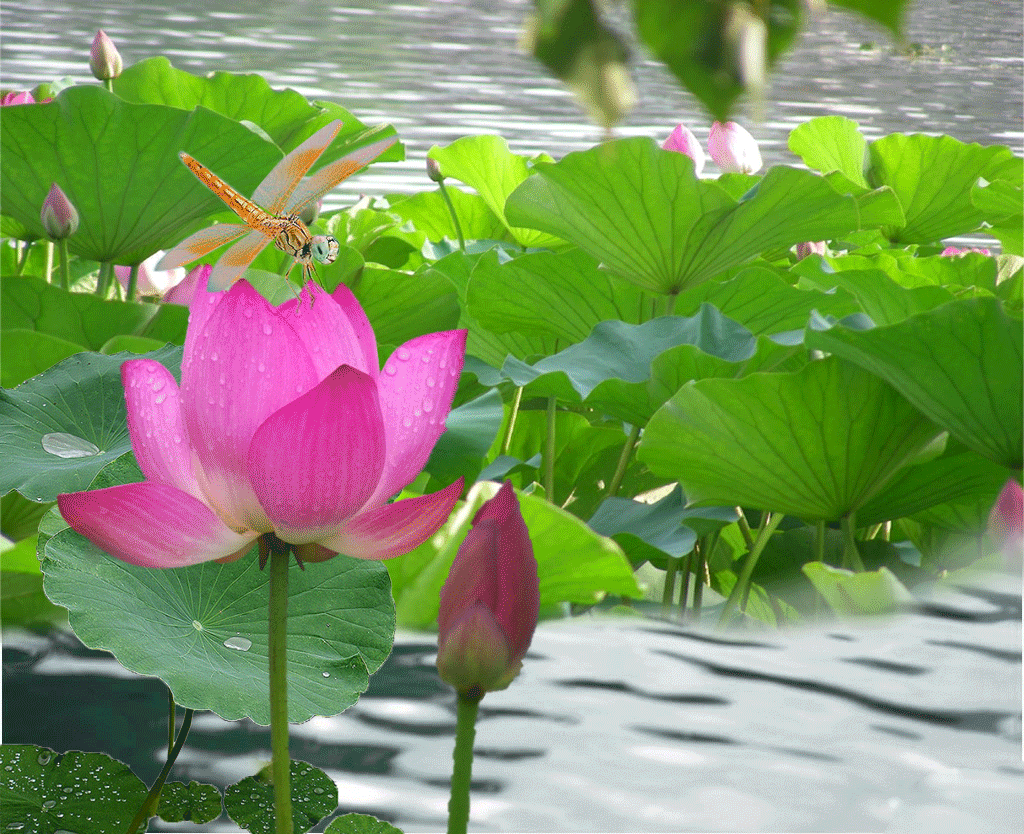
仇家坑最大,东北西南走向,椭圆形,几十亩大小,深处十几米之多,南岸较高,植有芦苇,漫延成势,芦花开时,白茫茫一片,且有垂柳相映,景观非常。北岸较低,有羊肠小道相连,缓坡可直至水面,为戏水之最佳场所。主坑往西尚配有副坑,名曰:西坑嘴子,虽说“嘴子”,亦有十几米宽,百米之长,中有沟连,有石拱小桥通过。天造地设,实为一景。因西坑嘴子较浅,里面埋有莲藕,盛夏时节,荷花盛开,菡萏如伞,彩蝶飞舞,蜻蜓戏水,杨柳婆娑,苇絮飘飞,蛙叫虫鸣,好不热闹,好不漂亮,天下美景,尚不过如此。

说,有水就有鱼。仇家坑,面那么大,水那么深,自然藏万千水族,说有簸箕大的老鳖,孩子大小的鲢鱼……坑是生产队的,鱼自然也是公有财产,每到春节将近,城头集的前天,生产队里就要逮鱼。赶在春节,那是让社员过个肥年;至于挑在城头集的头天,那是照顾会过日子的人家,分这么多的鱼不舍得吃完,趁鲜到城头集去卖,换个吃盐打油的钱。
那个季节是有冰的,用铁镐砸开,然后扛几个秫秸个子,并排捆了,上面放上门板,形如筏。“筏”上可立数人,有人执网,有人撑渡,只见撑渡人的长竹竿往岸上一捣,筏便向水中游去,几个筏子水中一搅,冰便慢慢化去,鱼便四处躲藏,成群结队的,看得见水纹,执网者皆选撒鱼高手,眼毒手准,迎着浪头一网撒去,便感觉沉甸甸的压手,知道收获颇丰,还要颤一颤网子,坑里撒鱼皆选大眼鱼网,水中一颤网绳,那是方便漏网之鱼,逃出去的多为鱼崽,那是为来年留下的种。

撒上来的鱼皆倒在用折子圈起来的洼地之上,银光闪闪,白花花一片,几斤,十几斤大小的都有,甚是喜人。围在一圈的孩子们手舞足蹈,不光眼看,尚且手摸,不小心就迸得一身腥水。我混迹于孩子们之间,看得是眼馋心热,竟不由得滴哒出了口水。突然心生歹意,何不偷拿一条,以缓解肚里的馋虫。那年月人穷,大多孩子的破袄里边是没有什么碎衣服衬的,称“乏筒子袄”。我便把乏筒子袄的下摆掖进了裤腰里边,糖牛似的。然后,手疾眼快,抓一条大小适中的,俗称斤半的鲤鱼,巧个,顺着脖子,丢进了怀中。不敢贪多,起身走家。没想到此举不是好活,那东西贴身放入,且冰、且滑、且粘、且瘆人、且动弹,本因天寒,已冻得奄奄一息,却被我体温暖得反阳,在我怀中摇头摆尾,肆意挣扎,扑楞楞乱动,又凉又怕,拿也拿不出,捂也捂不住,那种滋味,那种尴尬,难以描摹,终生不忘。
农村的坑,不光是鱼们的生长之所,亦是孩子们娱乐的天堂,那时候没有空调,连个电扇尚未时兴,整个夏日,孩子们是泡在水里的,三四岁时,便被邻居的大哥哥们拽到水里,喝几口坑里的泥汁水,是家常便饭,学会游泳也是无师自通。什么踩水,扎猛子,打迸迸,漂老窑……打迸迸就是文词说的狗刨;漂老窑,就是仰泳喽。漂老窑讲究把肚皮露出水面,能挺出自己的小鸡鸡,更属高手,亦是初学者的追求目标。再者就是爬到歪脖子柳树上,往坑里跳,属于高台跳水之类,个个把肚皮拍得通红,但绝没有喊疼的。周瑜黄盖,愿打愿挨

天旱季节,亦有水浅之时,记得西坑嘴子便分割出几个小坑,有邻居一大我四五岁的哥哥,人称“孩子王”,他手下领着一班人马,我亦在其中。一天,他说逮鱼,“战士们”便异常兴奋,跃跃欲试。便分配任务,各自从家中拿来脸盆、水桶、镢锨之类,到一较大水坑边沿,他说:这里边有鱼,看那波纹儿,鱼应不少,还定不小。于是就挖沟筑坝,用脸盆、水桶向外泼水,将沟挖深,向外放流。我终于明白,此曰:渴泽而渔。

伙伴们脱个净光,忙得不亦乐乎,水终于越来越少,显露出了庐山面目,竟格格秧秧大大小小,半池子之多,有黄鳝、鲶鱼、草鱼、鲢鱼、泥鳅……大家一声呼哨,跳入水中,那才叫“白手拿鱼”,盆舀桶捞,用杈头往水里一搭,就是半杈头活物。还有个伙计,扛来的镢头,就把他的裤子三头扎住,也灌了个满满荡荡。
家乡的水坑,我梦中的那串珍珠。

(二)南大寺
我们辛绪村,村前有河,曰:漷河。漷河在我们滕州界里也算一条大河,发源于东北凤凰山一带,流经岩马,筑坝成湖,便是鲁南知名的岩马湖了,然后顺势而下,由于强势,便有了“漷河夺荆”之说,下游便称之为荆河,或说城河。漷河对我们村十分恩赐,在我们村前任性地打了弯儿,便旋出来一片沙滩,一汪碧水。沙滩广而大,沙子细而白,儿时,光着屁股在沙滩里打滚,扎跟头,如躺在面窝里一般。渴了,便撅着腚往下扒沙,几下便能淘出水来,开始尚有些混浊,须臾,便清澈见底,将头伸进去,饮老牛一般,清冽而甘甜,瞬间便有一股清凉滋润到了五脏六腑。河南岸则是望不到边的野生芦苇,芦苇荡里藏着老鳖、螃蟹、野鸭,以及一些叫不上名来的水鸟,只是孩子们是不敢涉足的,大人说,里边有毒蛇,獾狗子之类,还有深不见底的淹子坑,淹子坑里有淹死鬼,掉到里边就爬不上来。

山南水北谓之阳,漷河北岸则是一大片树林,浓荫里藏着一座寺院——南大寺。名曰大寺,自然规模空前,明清之时,香火鼎盛。大雄宝殿,巍峨壮观,重檐拱厦,雕梁画栋,金碧辉煌。有大殿、二殿,东西厢房,还有供僧人住的后院,院内苍松翠柏,一口硕大的铜钟吊在一棵古槐之上,每日晨昏,便有寺内僧人撞钟,那悠扬钟音,传数十里而不灭。寺庙的大门是三间雕梁画栋的建筑,高大、庄严、肃穆,门两旁站立着哼、哈二将,粗壮的黑漆木柱上,用朱漆写就的一幅对联:“一尘不染清静地,万善同归般若门”。字体遒劲,不知出哪位名家之手。听老人讲,这幅对联的奇特之处,就是在很远的地方,看不到门两旁的柱子,却能看到这两行大字,哪怕是在大雨滂沱,哪怕是日落月明,在能见度极低的情况下,百米之外亦清晰可见。这幅神奇的朱漆楹联,为这座寺庙平添了许多神秘、庄严的色彩。
大殿内,供奉着普贤、文殊两位菩萨,两侧是十八罗汉,形态各异,栩栩如生。后院是次殿,供奉着送子观音,左右侍立着金童玉女。据说,这里的观音很灵,有求必应,因此前来求子香客络绎不绝。
村中老人尚言,不知哪座殿内,供一神像,村人们呼之“丧木神”,面目狰狞,口眼滴血,做过坏事之人,每每见之,心惊胆颤,六神无主,不自觉间,能将所做坏事合盘托出,百试百验。
院内有千年古树,数人合围,虬枝参天。门外有戏楼,农历四月初八为南大寺庙会,浴佛佳节,人物万千,苏鲁豫皖,邹滕峄沛,四省八县,齐聚郭河岸边。盛时,三台大戏对唱。实为鲁南之大观也。
南大寺的西南方向,尚有几座佛塔,虽尚未成林,也略有规模,七八座之多,有七层的,也有九层的,造型奇特,各有形态。那是高僧圆寂的墓地。也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南大寺规模宏大,及年代久远。
南大寺一说为唐朝所建,也有说建于宋金的,过去亦有残碑,现已不知所遗,因之无从考证,好在也无人较真,但传说兴盛时方圆数百里的百姓都来此供奉朝拜。还说,当年侵华日军也来过这座寺庙,进去观看了一阵子,挨个儿神像前皆顶礼膜拜,还前后照了好多相片,不知是出于敬畏,还是什么原因,一向烧杀抢夺的日本鬼子,竟对庙内陈设丝毫无损。这就更增加了这座寺庙的神秘和人们对它的崇敬。解放后,辛绪村划归城头乡公所,为了建高级社,乡公所的干部带领一伙人把它拆了用木料。又逢“文革”浩劫,南大寺几历尘劫,风雨摧残,人祸天灾,庙中古树珍木斫伐殆尽,古垣遗址荡然无存,但风水灵气仍隐隐可见。
据说,有南蛮风水先生,路过此地,流连驻足,徘徊良久不忍去,阳光下辛绪村,木茂而多古,地阔而能平,背山而凝重,面水而平阔,北望莲青逶迤,宛若虎踞,村前漷水奔流,势如游龙。天地氤氲,蒸腾笼罩,霞光紫气,缭绕其间,左高右低,观者悦目,玩者赏心,胜地也。长叹曰:“前有照(水),后有靠(山),两侧有抱,实乃风水宝地,不凡,不凡,将来待有才人出,定领风骚数百年……”
说完,又虔诚地拜了三拜,战战兢兢而离去。

没想到这个南蛮风水先生一语而成谶,这个远离县城,普普通通小村庄里,却涌现出了两个大名鼎鼎的企业:一为恒仁集团,一为辛化集团, 皆年利润十数亿元之巨。
这两家企业,从村中向外修了一条宽阔平坦的柏油大道,名曰:振兴路。村口立了一座硕大的石牌坊,正中“辛绪村”三个大字,两边撰联:辛化创新誉四海;恒仁诚信惠八方。
<hr> 
作者简介:梁子华,字秋实,大学学历。一九六二年出生于滕州市东郭镇辛绪村,一九八三年参加教育工作至今。毕业于滕县师范,后进修于曲阜师范大学,思想政治教育专业。酷爱文学、诗词、书法。 <hr>本文首发《 走进滕州》,转载旨在传播更多滕州地方文化。 | 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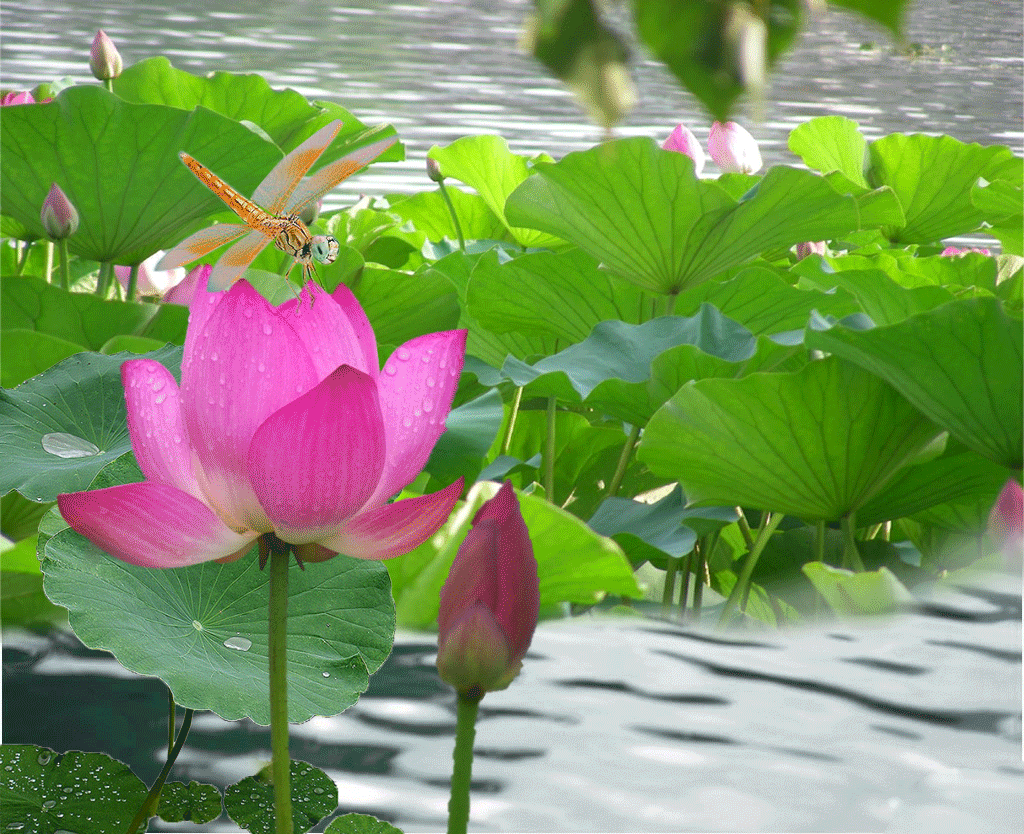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精彩评论文明上网理性发言,请遵守评论服务协议
共0条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