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香传娄凤 名德誉邹东——邹城田黄大峪口麟州张氏考略(马加学) 邹城市田黄镇大峪口村,东接凤凰山,南依娄凤山,西壤白龙池,北临小沂河。咸丰十年(1860年),这里爆发了文贤教(白莲教)起义,同治二年(1863年)秋,僧格林沁带兵镇压,清军所到之处,无论老幼,屠戮殆尽,屠杀义兵及民众三万有奇,白骨成堆,血流成河,尸横遍野,惨不忍睹,方圆十余里,村庄尽毁,土地荒芜,虎狼出没,不闻鸡犬。同治四年(1865年),张荣斋从政府领得邹东大峪口山地239亩,同治六年(1867年),他辞去沛县团务,归入邹东,同治十三年(1874年)秋,张荣斋举家从江苏沛县迁居大峪口。此后,张氏瓜瓞绵绵,螽斯振振,忠义传家,满门和睦,俊杰累挺,贤能辈出。张荣斋及其子张登岚,其孙张丕承、丕猷、丕振、家桢、丕矩,且耕且读,或医或武,设馆山中,教泽生徒,崇文习经,吟诗著述,张登岚、张丕承、张丕猷、张家桢、张丕矩,父子五人俱入县学,博取青衿,因此有“一门五庠生,父子皆秀才”之美誉,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,与孔孟嫡裔交往密切。 张良后裔,屡迁至邹 张氏先祖原居江苏邳州,相传为汉留侯张良后裔。至张升时,因军功起家,任校尉(家谱记载为武略佐骑尉,此官名清朝乾隆时才出现,应为误),明永乐四年(1406年),张升从江苏邳州徐唐社河东庄,迁居至巨野城东获麟堡张家楼,垦荒耕种,因巨野古有麟州之称,故其门称为“麟州张氏”。道光五年(1825年)四月,张荣斋(字耀亭)生于巨野张家楼,咸丰四年(1854年),太平天国军攻破巨野县城,他协助唐守忠在获麟堡办理团练,均粮分田,安民拒盗,一方得以保全。次年秋,黄河在河南兰考、仪封一带决口,河水淹没巨野全境,再一年又逢秋季大旱,咸丰九年(1859年),唐守忠、张荣斋遂率族人及团众迁至沛县昭阳湖边,在湖陵披荆斩棘,开垦荒地,筑圩修村,此处村名仍为张家楼。同治四年(1865年),捻军攻破团寨,团守唐守忠被杀,同时受到沛县当地排挤,张荣斋于是有了退隐之意,清政府镇压白莲教之后,将该地收为官地,正在进行组织迁民分地,张荣斋以为团练筹款名义奏请曾国藩,从政府领得邹东大峪口山地239亩,同治六年(1867年),他辞去沛县团务,归入邹东,同治十三年(1874年)秋,黄河再次决口,水灌昭阳湖,村庄被淹,张荣斋遂把家人从江苏沛县迁居至大峪口,开启了麟州张氏在田黄大峪口的新生活。光绪二年(1876年),52岁的张荣斋受沛县张家楼团民及族人恳请,返回沛县担任团务,光绪六年(1880年),再次辞谢团务,退老东山,回到大峪口,“以无欲养生,以和气接物,以读书垂训,以朴诚型家。” 孝友传家,忠义立身 自古以来,中国氏族基本都尊崇儒家“忠厚传家远”的治家思想,将忠孝礼义列为做人治家的首要,张氏家族亦是如此。据《张氏族谱》记载:张荣斋的祖父张凤居,能事父母孝,处兄弟友,轻财重义,周急扶困。兄弟四人分家时,以财让兄弟,后来家道中落,做起生意,将本求息,不取分外之财,有负债者,每焚其券,买地不论值。嘉庆十八年(1813年),岁大歉,人相食,富者多勒价购地,而张凤居却说:“似此凶荒,人惟急,故割卖血产以求活,多一文钱,则可多活一日,何为乘人之急,抑勒地价乎?”故以地来售者多增其价,如数与之,弗计其价。等到了丰年,官府发布告示,要求赎地,而人怀其家之德,所卖地无一赎者。其祖母也是性和善敦厚,歉岁时常施粥与饿者食,村里贫者周之无少吝。张荣斋父亲张学乾,因为父亲去世早,兄弟弱小,遂弃诗书梳理家计,延请老师教育兄弟,为兄弟操持婚姻等事,分家析居后,仍时常周济;对族中学子,资以膏火,笔墨纸张,丝毫不吝,对于学习优秀者,时常奖掖,遇有族中学子赴考会试者,给以盘缠。族中学子张登峰天资颖异,兼有勇智,张学乾认为可以成大器,最是器重他,张登峰后成为巨野一乡之师,张登岚、张丕承等都曾跟他读书习经。张荣斋在沛县协助办理团务期间,公正廉明,受到团民的拥戴。当时,捻军在青州、莱州一带活动,挟裹了一些青州、莱州子弟南下,在他们经过微山湖时,张荣斋不怕与捻军结怨,集合家族的力量乘机堵截,留下了一些青州、莱州子弟,并资助他们回归乡里。张荣斋去世后,其孙张丕承撰写一副长联,总结了他一生的功业和品行:“功在生民,率三千户荡析饿殍,越省过县,远垦湖荒,以推淤始,以用武终,只凭着愚忠朴信,冲开巨浪恶风,遂使数万人性命身家抛砖落地;德先庸行,闻六十年四书功深,孤意苦心,力辟蹊径,学在伦常,淡在势利,一任他内忧外患,当前沓来纷至,独能以夙夜问战警惕厉人回天。”清翰林院编修高熙喆在《耀亭张君墓表》中也赞道:“团中之人,至今思之,言大节者必曰唐公,言大德者必曰先生。”张丕猷在清末民国初年,看到社会动荡混乱,邹东一带盗匪群起横行,他于是弃文从武,加入民团,担负起御匪保民的职责,任四县联防西面总指挥,坐镇杨家峪龙山寨,他白天运筹帷幄,夜晚瞭望巡逻,连战皆捷,使得一方安然无恙。张丕振教读十余年后,也弃学为医,擅长妇科及温补之术,对一些久病不治之症,往往有奇方偏方,一药而愈,因此得到“仁医”美誉。清末民国初时,被选为邹县故老代表,赴省政府条陈利弊,道出人民心曲。张家桢也在1921年左右,看到邹东土匪猖獗,祸国殃民,他于是在大峪口一带修山寨、办民团,御匪保民。他还曾携款奔赴土匪老窝王村王家营,慰吊难民,并呈请上级,施赈救济,日寇侵略时,他在村南的楼凤山组织人员与日寇进行游击战。1928年,邹县大旱,禾苗半枯,民不聊生,他采集野草树叶,制成疗饥药丸,亲尝示范,百姓效法,方能得以活命。晚年创办同善社,恤苦怜贫,施与养邻,使百姓不至流离失所。生逢乱世,世事无常,他要求子孙学会忍辱退让,“不会吃亏学吃亏,不会吃气学吃气,终有好处。”张丕矩也是至诚爱国,1919年“五四”爱国运动波及到邹县,张丕矩组织青年学生召开庆祝大会,并发表了情绪激昂的演讲,号召师生员工、工商各界人士,投身于爱国运动中去,会后又组织了游行,在县内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。张丕矩处事公正,不畏权贵。民国初年任劝学所所长时,值旧县政府举行选举,地方官员徇私舞弊,他撰写了一幅对联给予了辛辣讽刺:选举本公道,道在人为,为得争名夺利;投票求完全,全在运动,动则祸国殃民。“七七”事变后,邹县沦陷,张丕矩毅然辞去小学校长职务。回邹东老家后,决心组织武装,保家救国,联合桃花哨的张景洲、瓦曲的聂秀轩、辛庄的王敬轩等人,成立了抗日自卫团,张丕矩亲任团长,于正月十五日在辛庄学堂召开了抗日自卫团成立大会。光绪二十二年(1896年),麟州张氏续修家谱,张荣斋在《家谱传序》中就写道:“后人思孝友之传家,则入孝出悌之心将油然升矣;思忠义之传家,则忠君报国之心将戚然动矣;思礼义之传家,则讲学明伦之心将奋然起矣;思创业之艰难及守成之不易,则食德服畴之念与光前裕后之心将恍然兴矣。”后来张氏一族续修世系时,经族中德高望重之人商议,特别将“孝友”二字写入其中:“昭明开景运,孝友衍世传,蕴光念先德,福泽自长延。”并以此作为其族人家训格言,以期后世子孙永志不忘。 习文业儒,设馆授徒 自张升迁居巨野,后世子孙读书习文,一直无断,虽无有功名者,但识文断字,知书达理。张凤居、张学乾,都是幼时业儒读书,但均因家庭困顿,不得不弃书理家。张荣斋8岁开始读书习文,11岁时父亲张学乾去世,26岁,入巨野县学成为附贡生,此后,张荣斋绝意科考,回到乡里当起了私塾先生,教授学生。二次辞去团务归入大峪口后,光绪九年(1883年),59岁的张荣斋在学馆中教读诗书,讲授程朱理学。在读书方面,他认为:“以读书专有志于利达,不求益于身心,切切为戒。”他教学生“以四书五经狠用功,不必专用力于文章,谓文章乃德之见乎外者也,是学问之绪余,道德学问深,文章自佳。”他曾赋诗告诫自己的学生:“读书身有益,岂专在功名。敬肆分狂圣,谦盈定吉凶。最宜存戒俱,切莫恃聪明。处处遵规矩,方称好学生。”邹县知事方龢评价他说:“耀亭公学宗程朱,尚忠信,励风节,求真知,重实行。”自张荣斋之后,张氏子孙习文读书,贤能辈出。张登岚,字晓山,生于1844年4月,8岁开始跟随张荣斋读书习文,他颖悟过人,涉猎广泛,12岁时黄河决口,就写下了“风月满前溪,云雷万户低”的诗句,14岁开始著《狐腋集》《管蠡集》,19岁转随李寿昌读书,24岁入巨野县学。到大峪口之后,他看到“邹东文学不兴,已数百年,致酿成教匪之乱,经民兴,则斯无奸邪。”光绪元年(1875年),32岁的张登岚开始在大峪口设馆授徒,邹东、滕东、费县一带的学生纷纷慕名上门求学,附近一些贫穷上不起学的孩子,他也尽量劝其上学,甚至还管吃管喝。当时一些私塾先生多注重辞藻文采,而轻视实际脱离生活,他却“以尚公尚实为宗旨,以无志无耻为切戒”。他给学生讲课时,精力旺盛,毫无倦色,讲解经史文章,纵谈中国大势时,每每议论风声,痛快淋漓;说到礼教文化衰微,社会风气颓败时,往往慷慨激,昂扼腕叹息。其忧国忧民思想,时常流露于言辞之间,学生们无不被他的精神感染,其中聂秀轩就是他的学生。61岁时,清政府实行新政,废除科举,兴办学校,当时的乡里人都觉得是一件怪异之事,仇视新学,唯独张登岚视为当务之急,他积极奔走,筹拨官产,捐款捐租,在辛庄设立国民高等小学,主动把自己的子孙和学生送入新学,亲自到该校当起老师。64岁才结束了教学生涯。张登岚学贯中西,从事教育事业三十余年,学生遍布邹滕巨沛费等地,教泽深入人心,1912年,69岁的张登岚去世。他去世后,其族后人撰写了一副挽联:“伤哉闻之,天地无情殒一老;呜呼往矣,兖曹何处访通儒。”高熙喆在《清乡饮大宾晓山先生墓表》中也说:“东方之学者,争执雉以趋,或携文字索点窜,辄速飞。由是而邑东之文学,遂蔚然以兴焉。”八年后,他的学生感念其品德,遂集资为他修建《张晓山先生教思碑》,并请邹县知事方龢撰写碑文,给予了张登岚较高的评价:“名山讲学,振聩发聋;以觉后觉,气象严凝。杏坛花浓,程门雪皎;善诱循循,无间昏晓;暗室孤灯,后进师表。先生教泽,历久弥新;英风盖世,遗爱载人。”张丕承,字伯述,亦字效翼,生于同治元年(1862年)6月,卒于1933年7月,享年72岁,光绪十年(1884年)考入巨野县学庠生,随后跟父亲张登岚设馆授徒,先后教授邹滕沛费之地的学生二百余人。巨野增生王槐卿在《张伯述先生教思碑文》中说:“门盈桃李,共乐春风,室入芝兰,同沾化雨。”“孝泽绵延兮作育才之时雨,文光灿烂兮挂聚奎于德星。”张丕猷,字仲勋,生于同治三年(1864年)12月,光绪十三年(1887年)入巨野县学庠生,卒于1933年12月,享年69岁。他曾拜高熙喆为师学习,在学习上也是深受父亲影响,讲求实用,深通经济学,以明伦为主旨,明体达用为先务。张丕振,字叔作,生于同治七年(1868年)10月,卒于1939年4月,享年71岁。他写的一手新颖文章,但是文章写的慢,没有进入县学,仅得代守备衔,教读十余年后,弃学为医。张家桢,字海秋,生于同治十三(1874年)年10月,卒于1951年10月,享年78岁。他读书非常刻苦,读经史子集,往往探本求源,经常独坐默思废寝忘食,精于天文算术、大清律,光绪二十七年(1901年)考取邹县庠生。教读为业,常常教导勉励学生:“人所难知者己知之,人所难能者己能之,学有所长,斯为贵耳。”后转学新学,毕业于山东农林学院,民国时期,在曹州郯城滕县邹县学校教员、校长,后任邹县劝学所所长、农林蚕业技术员、建设局秘书等职。抗战时期,在大峪口山中设立大同学校,以教得民。张丕矩,字季方,生于光绪三年(1877年)7月,卒于1964年,享年88岁。他幼时先后跟随父亲及长兄读书,他厌恶八股文,崇议论,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考取邹县庠生,四书五经默然贯通,善于历史考古,精于考据、中外地理等,后转学新学,毕业于山东农林学院。一生主要是从事教育教学工作,1908年创办田黄初等小学堂,1913年任邹东劝学所员,1917年任县劝学所所长,1921年被选为邹县教育会会长,并任县立女子小学校长,1925年任县通俗讲演所所长,1930至1937年,先后在城前村、水泊村、莫亭村、柳下邑、姜家窝等小学任教师,1938年邹县沦陷后,曾应聘任书院小学校长,因不愿为日本人效劳,任职仅两个月就愤然辞职,1938年同张家祯在文庙内创办崇孟学社,执教6年,1944年后受聘任滋阳县师范和滋阳县中学教师,并兼设在滋阳县的天主教神学院教员。1950年回家乡时己73岁高龄,这时农村正大办冬学,他自荐当扫盲教员,教家乡农民识字。他还自筹钱款,立孔孟诞生地碑。晚年乐读书,手不释卷,研究革命文学,新中国成立后,任山东省文史馆馆员、邹县人民委员会委员。 著书立说,吟诗赋文 1934年,张家氏族曾刊印了一本《张氏家学》,里面收录了诗文90首(篇),其中张荣斋8首,张登岚16首,张丕承6首,张家桢4首,张丕矩2首。张荣斋晚年深居山中,读书参禅,不问世事,生活恬淡自如,他在《即境写怀五十韵》写道:“室陋堪容膝,亭高最豁眸;参禅凭几案,携卷倚松楸;牧曲闻长岭,樵歌出暗陬;惊心观日昃,快意看云收;即喜居山静,能嫌入谷幽;勿论谈富贵,并不计沉浮;利欲胸前绝,存亡脑后丢;天伦欣得所,率性乐悠悠。”在《步韵写怀》写道:“何年熬得尘缘尽,笑倚柴门看古松。”在《归山口占》写道:“而今稳坐回头岭,哪管南风与北风。”此外还撰写了一些对联,如:“山静似太古,日长如小年。”“身安茅屋稳,性定菜根香。”晚年著《清虚老人训言》,几十年后,其孙张家桢还在文章中回忆说:“捧读遗训,见心长语重,义正辞严,皆足垂范百世。”张登岚著有《管蠡集》《周易集腋》《家礼集腋》《家规集腋》《稼穑说》等。民国《邹县新志》中,还列出他撰写的《痴人记》一册、《阐关图说》四卷、《各省形势考》三卷、《沿海七省图说附考》四卷,可惜只有条目。他的诗多咏古诵贤,以此表达他的壮志和抱负,在《咏史》中写道:“吾慕唐邺侯,白衣辅肃宗;吾慕汉留侯,功成访赤松;隐居求其志,文史足三冬……大展经纶手,霖雨沛四封;不贪富与贵,归去老碧峰。”在《微山湖即景抒怀》写道:“砥柱中流任客游,微湖山上拜留侯;百川欲障东之水,未识狂澜可倒否?”在《曹郡书怀》写道:“济世常留万古新,高川流水待知音;丁年思上金门赋,午夜学为梁父吟;止道范公胸有甲,谁知管子腹有壬;襕衫脱却归山去,明月清风惬素襟。”在《邳州怀古》写道:“心思报国求椎击,志在匡时借箸筹。”在《咏冯谖》写道:“茫茫天下无知己,徒使英雄唤奈何。”但由于生活在国局动荡时运多舛的时代,他的理想又难以抒展,内心的苦闷也只能述诸于诗端,在《微山湖即景抒怀》写道:“青笠绿蓑识故吾,渔山樵水是良图;风尘扰攘难容足,万里烟波一钓徒。”在《曹郡书怀》写道:“从来富贵不可求,困穷岂是吾儒忧。居邹久凛圣贤训,天不怨兮人不尤。”在《题挟琴访友》写道:“高山流水知音少,风入谷松乌夜啼。”张丕承也好咏史,他感慨当时时局动荡,思想混乱,遂借助对黄帝时代的歌咏表达他对和平的向外和对时局的批判:“龙战初闻戮蚩尤,安民定制乐悠悠;征诛禅续多神圣,还让轩皇在上头。”他在《登青莲阁》写道:“我来正逢秋气清,日射金波万点明;一杯奉酬高阁上,傲骨至今属先生。”诗中也是他自己“有至性”的表达。作为张良后裔,他为留侯写下了十首诗,在对留侯的仰慕之间,也透出了他的理想,其一写道:“博波沙中击暴秦,当年刘项尚潜身;输他先试英雄手,此后亡秦第一人。”另一写道:“力士铁锤古莫闻,当年一击气凌云;不因附骥声名显,万古谁知沧海君。”民国《邹县新志》中,也列出了他撰写的《君子言行录》、《抗坏高尚录》、《退庵笔记》书目。张丕猷晚年精研理数,诠注四书,著有《学庸》《论语诠注》等书。他在《春兴》写道:“功名富贵总成空,象外超身入个中;笑看浮云翻上下,闲参指爪印西东;羹墙日月光华灿,琴梦音容生气通;显晦升沉应有定,歌咏风浴乐融融。”张家桢著有《忠恕堂文存》《反省录》《应酬类编》等书。他的《勖诸生》之一:“博学仰尼山,至圣兼多能;德行与道艺,大小并包容;俗学渐失真,一得每自矜;摒弃经世务,耳目塞聪明;振衰赖俊杰,力卓识尤精;兼集众所长,儒宗慕大成。”之二:“殚精鹜八极,积累由铢寸;二十世纪中,争胜在学问。”之三:“羽毛未满丰,高飞忽倾倒;一朝六融成,翱翔九天表;几见鸿与鹄,终身困池沼;矫首海天遥,下学苦不早;但惜业未精,勿谓知音少。”他晚年修建了乾元洞,在此读书参禅,写下《乾元洞落成述怀八首》,其中有句:“闲从世外觅桃源,柳暗花明隐石门;飞瀑作簾山作壁,红尘满断一乾坤。”“杖藜扶我过前川,不见夭桃映日鲜;一样风流飞绛雪,参禅人坐杏花天。”张丕矩爬山越岭,跑遍全县,历尽艰辛,在民国六年(1917年)完成了《邹县地理志》的编写任务,后于民国三十一年(1942年)又增写“邹县地质”一章。《邹县地理志》一书,是张丕矩先生给全县人民留下的一部有价值的历史文献,同时他还著有《峄阳文献录》《四部辞选》《图注城守篇》等。如今他的诗文大多散失,《张氏家学》中仅收录其诗两首,录其《夏夜》:“雨息孤村暮,炎蒸暑气平。绛霞天外落,凉意树中生。涧下蛙声急,山头月色清。宵深浑不寐,坐到夜三更。”诗文清丽淳朴,足见功底深厚。 总之,自同治十三年(1874年)秋,张荣斋挈家迁居至大峪口,祖孙三代在文化教育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,张荣斋、张登岚、张丕承、张丕猷、张丕矩等俱入《邹志》,新中国建立之后,更是家族繁盛,人丁兴旺,如今已达三百余人,后世子孙均能恪守家言祖训,读书修身,忠义爱国,代有贤能,其中不乏优秀者。据其家谱记载,宝字辈中如:张宝图,民国时期曾任邹县教育局长;张宝树,能诗能文;张宝珊,民国初期创办邹县人民自卫团,任第七团团长、田黄联庄会会长。中字辈中如:张中良、张中藩、张中美、张中兴、张中旭等烈士;张中路,团级参谋长。昭字辈中如:张昭泉,师级干部。明字辈中如:张明达,曾任邹城市人大副主任。其他在党政机关、部队、教育等战线工作的人更是不胜枚举,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敬业奉献。大峪口麟州张氏一族,150年间一直以读书习文传家,以孝友忠义立身,张中仁在1983年续修家谱时写道:“光前裕后前程远,孝友二字为根恒。道德功业人敬重,流芳家谱最上层。”户居娄山常住凤,门迎云磨久停麟。斯人虽已去,书香仍传娄凤山;后世犹可追,名德继续大峪口。 | 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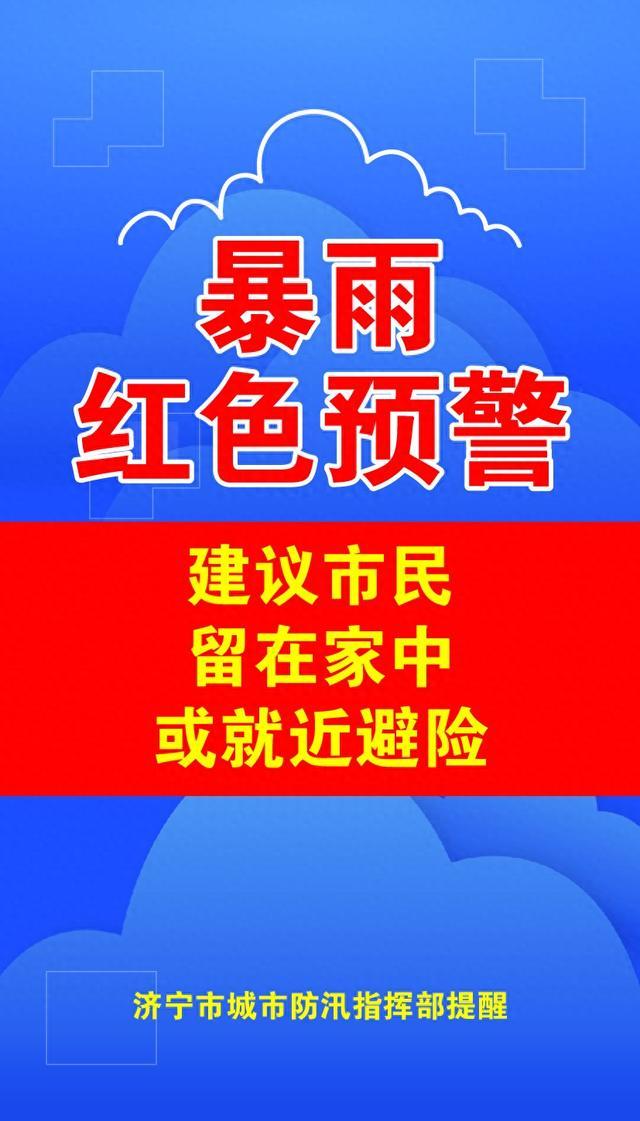







精彩评论文明上网理性发言,请遵守评论服务协议
共0条评论